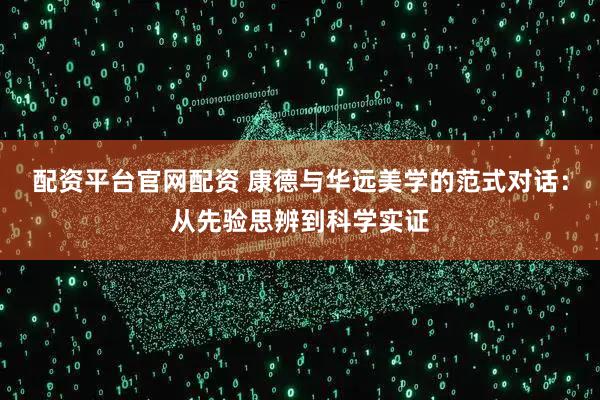
油画《聚集》作者为华远配资平台官网配资
康德与华远美学的范式对话:从先验思辨到科学实证
作者为华远
写于2005年3月配资平台官网配资,修改于2025年9月
摘要
本文聚焦康德美学与华远科学性美学,基于《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及《康德与华远美学的范式对话:从先验思辨到科学实证》核心内容,从美本质界定、审美判断依据、方法论基础、实践应用等多个维度展开系统对比。康德以先验哲学为依托,提出 “审美无利害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等核心命题,着重强调审美判断的主观性与普遍性;华远则以 “信息中介” 为核心构建起 “三定六位一体”“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的科学性框架,整合了哲学思辨、文艺经验与科技实证。特别针对崇高美论,华远以 “膨胀模式” 为核心,兼容互补、切近、缓冲等多元机制,形成动态立体的审美系统,突破了康德 “理性超越” 与黑格尔 “理念显现” 的线性局限。通过分析两种理论对自然美与艺术美、自由与自律等问题的解答,揭示美学从抽象思辨迈向科学实证的演进逻辑,并探讨其对当代审美实践的指导价值。文章力求语言平实,尽量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展开剩余97%关键词
康德美学;华远科学性美学;信息中介;审美判断;时空定位;红绿蓝三维度;崇高美;膨胀模式;四维动态
前言
自鲍姆嘉登为 “美学” 命名以来,“美是什么” 这一问题便如同美学领域的灯塔,吸引着无数研究者驻足探索。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以先验哲学为骨架,将审美活动界定为 “主体的自由判断”,为西方美学奠定了深厚的思辨传统;而华远提出的科学性美学,则试图打破传统美学的形而上学桎梏,通过 “信息中介”“时空定位” 等概念,将美学研究纳入跨学科的科学框架。
本文立足《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与《康德与华远美学的范式对话:从先验思辨到科学实证》相关研究资料,以平实的语言解析两种美学体系的核心差异,尤其聚焦崇高美论的范式分野。通过引用康德等哲学家的经典论述,结合《暮色》《静静顿河》《平凡的世界》等文学案例及校园升旗、医生献血等日常审美实证,展现美学从 “先验闭环” 到 “科学开放” 的演进轨迹,帮助读者在理解理论的同时,学会用多元视角分析现实中的审美现象。
一、引言:两种美学范式的理论基石
(一)康德美学的先验框架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构建了以 “审美判断力” 为核心的先验哲学体系,其理论支柱建立在对 “知、情、意” 三大心灵能力的划分之上。他认为,审美判断力是连接纯粹理性(知识)与实践理性(道德)的桥梁,具有独特的 “中介性”。
审美判断的特殊性在于,康德强调其是 “主观的、感性的”,不依赖概念与逻辑。“鉴赏判断完全不系于客体的存在,而只在乎对象的形式如何呈现于主体的感知”,当我们欣赏一幅描绘田园风光的画作时,无需知晓绘画技巧或创作背景,仅凭画面的色彩搭配和构图就能产生美感。这种判断区别于逻辑判断(如 “这是一幅油画”)与道德判断(如 “这幅画传递了善良”),是一种 “无概念的愉悦”。
审美体验包含 “感性享受” 与 “理性反思” 两个层面。以聆听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为例,旋律带来的听觉愉悦是感性层面;而在愉悦中体会到的 “形式和谐” 与 “心灵自由”,则是理性反思的结果。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写道:“美是两种心意机能 —— 想象力与知性 —— 的自由游戏。” 这种 “自由游戏” 既非单纯的感官刺激,也非严谨的逻辑推理,而是感性与理性的和谐共振。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是康德美学最具标志性的观点。他认为,审美活动没有实用目的(如欣赏一朵花不是为了让它结果),却能感受到客体形式 “仿佛” 符合某种目的。“自然的美暗示着一种合目的性,这种合目的性无需预设一个目的”,山间的溪流虽无 “供人观赏” 的实际目的,但其流淌的形态、发出的声响却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和谐,仿佛是为满足人类的审美需求而存在。
(二)华远科学性美学的开放体系
华远的科学性美学突破了传统美学的主客二分框架,以 “信息中介” 为核心构建了动态开放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包括三大要素:
“三定六位一体” 框架:“三定” 指时空定位(审美对象所处的历史与空间语境)、良性循环(自然规律与人文诉求的动态平衡)、矛盾统一(整体性与简洁性的辩证关系);“六位” 涵盖时空、循环、整体、简洁、信息、中介六大要素,共同构成审美判断的标准。例如,评价福建土楼的美,需考虑其客家文化背景(时空定位)、居住功能与文化传承的平衡(良性循环)、单个土楼的结构与整个族群聚居的布局(矛盾统一)。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模型:以 “良性循环” 为核心(一元),整合时间维度(审美对象的历史演变)、物质与精神多层级(如传统服饰的面料与象征意义)、文化历史多线索(如京剧艺术与民间故事)。分析《千里江山图》时,既要关注其宋代的创作背景(时间)、颜料和纸张的物质特性(物质),也要理解其承载的文人情怀(精神)与中国山水画史脉络(文化线索)。
信息中介的双重性:显在中介指可直接感知的形式(如雕塑的造型、诗歌的语言),潜在中介指隐性的意义(如文化传统、情感记忆)。中秋节的月亮(显在中介)不仅是一个天体,更承载着 “团圆” 的文化意义(潜在中介),两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审美对象。正如 “美是显在形式与潜在意义通过信息中介的共振”。
(三)崇高美论的范式分野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以 “理性超越” 构建崇高的单线结构,将崇高分为 “数学的崇高” 与 “力学的崇高”,强调感性挫败后理性对无限性的统摄(如星空的广袤触发对理性能力的确认)。这种 “感性→理性” 的线性超越,本质是理性对感性的单向征服。《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中提到,康德的崇高是 “理性对感性的单向征服”,主体通过抽象思维将不可把握的对象转化为可理解的理念,最终在对自身理性能力的确认中获得崇高感。
华远则突破线性思维,提出崇高是 “真(自然规律)与善(人文价值)的动态共振”,其核心的 “膨胀模式” 通过 “真善同频扩张” 引发能量爆发(如黄河壶口瀑布的流体力学法则与民族精神象征形成共振),同时兼容互补模式(自然与人文的非对称共生)、切近模式(主客情感频率匹配)、缓冲模式(意义留白的弹性调节),形成多模态复合的 “四维动态” 系统。《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指出,华远理论突破了康德 “理性主导” 与黑格尔 “理念优先” 的困境,将崇高从哲学思辨拉回文本实践,“活着就是奉献,健康就是美好” 作为华远科学性美学的核心审美价值观,深刻揭示了日常生活中崇高的伦理根基。
二、康德先验美学的核心命题
(一)审美无利害性的内涵与局限
康德提出的 “审美无利害性” 是其美学理论的重要支柱。他认为,审美判断不涉及任何功利性的考虑,只是对对象形式的纯粹观赏。当我们欣赏一件艺术品时,不会去思考它能带来多少经济利益,也不会去考虑它是否符合某种实用需求,仅仅是因为其形式本身引发了我们的愉悦感。
然而,这一命题也存在局限。黑格尔曾指出,完全脱离利害关系的审美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例如,人们在欣赏一座古代宫殿时,很难完全摆脱对其历史价值、建筑成本等方面的考量,这些因素或多或少会影响对宫殿美的感知。
(二)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
康德认为,审美过程是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想象力能够摆脱知性的束缚,自由地组合和创造表象;而知性则提供了一定的规则和范畴,使想象力的活动不至于陷入混乱。这种自由游戏产生的愉悦感就是审美体验的核心。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审美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们的这种自由游戏能力,从而实现人性的完善。例如,在欣赏一首诗歌时,想象力可以自由地驰骋于诗歌所描绘的意境之中,而知性则帮助我们理解诗歌的语言和结构,两者的和谐互动让我们感受到诗歌的美。
(三)崇高论中的理性霸权
康德的崇高理论以 “理性主导” 为核心,数学的崇高通过 “无限大” 的感官不可把握性倒逼理性建构抽象理念(如山脉绵延触发对 “无限” 概念的统摄);力学的崇高则以自然力量的威慑(如狂风暴雨)反衬道德意志的超越性。这种 “感性无能→理性胜利” 的叙事,将崇高简化为理性对感性的压制,忽视了主客交互的复杂性。
正如《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中《暮色中的崇高》所言,康德的崇高是 “理性对感性的单向征服”,主体通过抽象思维将不可把握的对象转化为可理解的理念,最终在对自身理性能力的确认中获得崇高感。但这种理论难以容纳日常实践中感性与理性的共生(如医生献血中个体情感与道德责任的交融),将崇高局限于哲学思辨的范畴,脱离了具体的生命体验。
在《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面对顿河的广袤时,感官的 “无能” 与理性对 “哥萨克命运” 的抽象思考形成张力,这一案例印证了康德数学崇高的 “感性挫败 - 理性超越” 过程。然而,“活着就是奉献” 的朴素理念,在康德框架中被简化为理性对 “利他行为” 的概念建构,忽视了奉献作为生命本能的感性维度,体现出其理论的局限性。
三、未竟之问:审美普遍性如何跨越 “物自体” 鸿沟?
(一)康德的两难困境
认识论断裂: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存在着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划分。审美判断仅能作用于现象形式(如事物的形状、色彩等),而无法触及物自体层面的美本质。这就导致了审美判断的 “普遍性” 实际上只是一种主观预设,如 “共通感” 的存在就是一种悬设,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四契机的矛盾:康德的审美判断第四契机强调审美具有必然性,但物自体的不可知性又使得这种必然性难以得到确证。Allison 在《康德的自由理论》中指出,康德美学隐含着 “形式主义陷阱”,过于强调形式的作用,而忽视了内容与意义对审美的影响。
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提出,康德美学的革命性在于将审美判断建立在人类主体性的先验结构之上,他强调,共通感的本质是 “人类实践中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 - 心理结构”,而非纯粹的先天预设。通过先验综合将现象界的 “美感”(如对自然对称的愉悦)与物自体的 “美本质” 隔绝。这种割裂恰显局限:动物仅有类审美本能(如雄鸟饰羽求偶),而人类能借先天理性为现象赋予意义(如将星空美感升华为对宇宙秩序的思考),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但康德未察觉,“美感” 与 “审美对象” 实则是 “时空定位” 中的动态信息中介:如对《大卫》的美感,会随文艺复兴人文语境与当代艺术视角的时空变化而调整,审美对象也非固定客体,而是显在造型与潜在人文意义的动态耦合,这也为华远以 “时空定位” 破解物自体困境提供了理论衔接点。
(二)华远 “信息中介” 的破局路径
取消主客二分:华远将美本质重构为 “主体 - 信息 - 客体” 的动态交互网络,就像量子纠缠态一样,观测行为本身会改变 “美” 的显现形态。这种观点打破了传统的主客二分模式,强调美是在主体、信息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中生成的。
时空定位的实在性:以山西平遥古城为例,古城的建筑布局(客体层)、晋商文化符号(信息层)、游客的历史认知(主体层)构成了一个可验证的审美链条。通过对这些层面的分析,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平遥古城的美是如何在时空定位中形成的。
四、美本质的界定:从 “主观合目的性” 到 “信息中介系统”
(一)康德:美是主体的 “主观合目的性”
康德否认美是客体的固有属性,认为美是主体对客体形式的 “主观合目的性” 判断 —— 客体的形式恰好契合人类的认知结构,引发无利害的愉悦。“鉴赏判断仅仅是静观的,它不带来任何关于对象的知识,只把对象的形式与主体的心意机能联系起来”(《判断力批判》)。
例如,对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的欣赏,与雕像的市场价值、历史背景无关(无利害),但雕像的比例、线条却与人类对 “和谐”“力量” 的感知需求相契合(合目的性),这种契合感就是美的本质。康德强调,这种 “合目的性” 是 “主观的”,不涉及客体的实际用途,仅体现主体心灵的自由状态。
这种观点的局限在于将美完全归于主体感受,难以解释为何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人会对同一对象产生相似的审美判断(如对日出的普遍赞叹)。正如 “康德未能说明‘主观感受’如何具有跨主体的普遍性,只能诉诸‘共通感’这一先验假设”。
(二)华远:美是 “时空定位与良性循环中的信息中介”
华远突破了康德的主客二分框架,将美定义为 “时空定位与良性循环框架下,整体性与简洁性矛盾统一的信息中介系统”。这一定义包含三层内涵:
首先,美是 “信息中介”,连接主体与客体。龙门石窟的美,既不在石窟的岩石本身(客体),也不在观者的主观感受(主体),而在石窟的佛像造型(显在中介)与佛教文化(潜在中介)共同构成的信息系统中。
其次,美依赖 “时空定位”。同一处古镇,在古代商人眼中是贸易的驿站,在当代游客眼中是历史的遗迹,因时空语境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审美意义。
最后,美需满足 “良性循环”。哈尼梯田的美,既符合自然的生态规律(水流走向、土壤保护),又满足人类的农耕需求和审美诉求,实现了自然与人文的动态平衡。
华远的定义克服了康德的主观主义局限,将美视为 “主客体通过信息中介的互动过程”,更能解释审美现象的复杂性与历史性。在崇高美领域,这种差异尤为显著:康德将崇高的本质归于理性对感性的超越,华远则认为崇高是 “真善信息在四维时空中的动态共振”,其核心的膨胀模式通过 “超尺度的真善结合”(如埃及金字塔的物理体量与神性崇拜的结合)构建审美能量体,同时兼容其他模式(如悲剧中命运必然性与人性尊严的互补共生),形成立体的崇高体验(《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
五、审美判断的依据:从 “共通感” 到 “三定标准”
(一)康德:以 “共通感” 为基础的普遍性
康德认为,审美判断虽为主观,却具有 “要求每个人同意” 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源于人类共有的 “共通感”。“我们必须预设一种共通感,否则知识与情感的普遍传达便是不可能的”(《判断力批判》)。
例如,莫扎特的《安魂曲》,无论听众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庄严与肃穆,这种跨文化的共鸣便是 “共通感” 的体现。但康德强调,这种普遍性 “不是通过概念来保证的,而是通过情感的共鸣”,与科学判断的客观普遍性(如 “地球绕太阳转”)截然不同。
然而,“共通感” 是一种先验假设,无法被经验验证。当不同文化对同一对象产生审美分歧时(如东方文化中白色象征纯洁,西方文化中白色有时象征哀悼),康德难以解释这种分歧的根源,只能将其归为 “共通感的不完善显现”。
(二)华远:“三定” 框架下的综合判断
华远提出 “三定” 标准,为审美判断提供了可操作的依据,克服了康德 “共通感” 的模糊性:
时空定位:审美判断需锚定对象所处的历史与空间语境。元代倪瓒的山水画,以简洁的笔触和空旷的构图营造出孤寂的意境,这种美只有结合元代文人的避世心态才能理解;若用现代写实绘画的标准去评判,便会产生时空错位。
良性循环:审美对象需实现自然规律与人文诉求的平衡。上海外滩的建筑群,不仅在建筑风格上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色(形式),更在功能上满足了商业、旅游等多种需求,同时承载着上海的历史记忆(文化),形成 “形式 — 功能 — 意义” 的良性循环。
矛盾统一:审美对象需实现整体性与简洁性的辩证统一。贾平凹的《秦腔》以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浓郁的地方风情(整体性)展现了乡村的变迁,同时通过秦腔这一简洁的文化符号(简洁性)贯穿始终,在矛盾中形成强大的审美张力。
“三定” 标准将审美判断从 “不可言说的情感” 转化为 “可分析的系统”,如评价一部电视剧时,需考虑其播出时代的社会背景(时空定位)、剧情发展与观众情感的共鸣(良性循环)、叙事结构的简洁与主题的完整(矛盾统一),比康德的 “共通感” 更具实践指导意义。在崇高美判断中,这一标准同样适用,如评价《暮色》诗中 “风雨中牵手” 的崇高,需结合诗歌的创作背景(时空定位)、自然力量与人文情感的平衡(良性循环)、意象的整体性与象征的简洁性(矛盾统一),从而全面把握其审美价值。
六、审美体验的构成:从 “感性与理性” 到 “显在与潜在中介”
(一)康德:感性享受与理性反思的交织
康德认为,审美体验是 “感性” 与 “理性” 的和谐融合,两者缺一不可。“鉴赏判断要求两种表象能力的协调:想象力的自由与知性的合规律”(《判断力批判》)。
以欣赏罗丹的《思想者》为例,首先感受到的是雕塑的肌肉线条和力量感(感性享受);进而会思考作品所体现的 “人类对真理的探索”“对命运的沉思”(理性反思)。这种体验既非单纯的感官刺激(如口渴时看到水杯的愉悦),也非冷静的逻辑分析(如从解剖学角度研究人体结构),而是 “感性中渗透着理性,理性不压制感性”。
康德的观点揭示了审美体验的复杂性,但他将 “感性” 与 “理性” 的界限固定化,未能解释两者如何在具体审美活动中动态转化。例如,面对一首现代诗,有人可能完全无法理解其内涵(只有感性),有人可能过度解读其意义(只有理性),康德难以说明这种失衡的原因。
(二)华远:显在与潜在中介的共振
华远将审美体验视为 “显在中介”(形式感知)与 “潜在中介”(意义联想)的共振过程,两者通过 “信息传导机制” 实现互动:
感知层:捕捉环境信号。欣赏陶渊明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时,首先感知到 “菊花”“东篱”“南山” 等视觉意象(显在中介)。
处理层:关联潜在意义。将这些意象与隐逸文化、自然情怀等文化记忆(潜在中介)相联结,理解诗句的情感内涵。
表达层:生成审美意义。在感知与联想的基础上,体会到 “闲适” 的审美特质,完成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化。
例如,长城的美,既在于其城墙的雄伟、关口的险峻(显在中介),也在于其承载的 “抵御外敌”“民族精神” 等历史文化意义(潜在中介),两者的共振让长城既 “壮观” 又 “厚重”。
华远的观点比康德更具动态性:显在与潜在中介的比例可随个体经验、文化背景变化。同是长城,建筑学家可能更关注其结构设计(显在),历史学家可能更关注其历史作用(潜在),两种体验都是合理的,体现了审美的多元性。
在崇高审美体验中,华远的 “显在与潜在中介共振” 理论体现为多模式的协同:膨胀模式主导 “真善超越” 的能量爆发(如《暮色》中 “风雨中牵手” 的意象既展现自然力量的威慑,又凸显家庭情感的崇高);切近模式实现主体对 “无限” 的情感共鸣(如面对浩瀚星空时渺小感与敬畏感的频率匹配);缓冲模式则通过意义留白(如崇高体验后的静默反思阶段)避免审美疲劳(《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这种多模态共存,突破了康德将崇高体验简化为 “理性反思” 的局限,更贴合《静静顿河》中葛利高里面对顿河时的复杂情感 —— 既有感官对自然广袤的震撼,也有理性对哥萨克命运的思考,更有感性与理性的动态交织,展现出崇高体验的丰富性与立体性。
七、方法论差异:从 “先验演绎” 到 “红绿蓝三维度”
(一)康德:依赖先验哲学的逻辑推演
康德采用 “先验演绎” 的方法,从 “人类认知的先天条件” 出发构建美学体系。他不关注具体的审美经验(如这幅画为何美),而追问 “审美判断何以可能”,将答案归于 “时空直观”“范畴形式” 等先验结构。
这种方法的优势是逻辑严密,如从 “审美无利害” 推导出 “审美具有普遍性”(因排除了私人利益的干扰),再推导出 “美是道德的象征”(因两者都具有普遍性)。但缺陷是脱离经验实证,“先验范畴” 如同 “黑箱”,无法被观察或验证。“康德用‘先天’解释一切,却未能说明‘先天结构’从何而来,陷入了‘以未知解释未知’的循环。”
例如,康德无法用实验证明 “人类对对称形式的偏好” 是先天的,还是后天文化习得的;只能断言 “这是先验审美判断力的体现”,缺乏说服力。
(二)华远:整合红绿蓝三维度的跨学科实证
华远提出 “红绿蓝三维度” 方法论,实现了从思辨到实证的跨越:
红色维度(哲学思辨):将康德的 “理念” 解构为 “形式粒子性” 与 “意义波动性” 的量子叠加(类似光的波粒二象性)。分析《战争与和平》的美时,既关注其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形式粒子),也关注其蕴含的历史思考、人性探索(意义波),两者在审美中形成 “量子纠缠”。
绿色维度(文艺经验):用 “光缆线橄榄型结构” 分析文艺现象。以中国当代诗歌为例,朦胧诗的先锋探索与乡土诗的大众表达处于橄榄的两极(创新极值区),而融合两者特点的诗歌则在中间区域被广泛接受,呈现 “创新与共识” 的动态平衡。
蓝色维度(科技实证):借助神经科学验证审美规律,如观看徐悲鸿的《奔马图》时,大脑视觉皮层与情感中枢同步激活,为 “形式与情感的互动” 提供生理证据;用量子力学 “波粒二象性” 解释 “形式与意义” 的关系 —— 形式是 “粒子”(确定),意义是 “波”(不确定),审美是两者的互动。
这种跨学科整合使美学从 “感性学” 升级为 “科学的感性学”,“既保留哲学深度,又扎根经验实证,实现了美学的范式革新。”
在崇高美研究中,华远的 “红绿蓝三维度” 形成完整闭环:红色维度(哲学思辨)解构康德 “理性超越” 的线性逻辑,提出 “真善矛盾→能量转化” 的辩证关系(如悲剧中 “命运无常” 与 “人性尊严” 的矛盾,经信息中介转化为崇高能量);绿色维度(文艺经验)以《暮色》“明暗交界线” 分析多模式协同 ——“荒凉与辉煌” 的视觉对比(显在中介)与 “时间流逝” 的集体记忆(潜在中介)共振,既体现真善膨胀(自然与人文的超尺度结合),又包含光影与情感的互补;蓝色维度(跨学科原理)引用神经美学原理阐释崇高体验的生理基础(杏仁核与下丘脑的联动引发情感波动),但不依赖实验数据,仅以 “健康个体对崇高的感知更敏锐”(如孙少平在煤矿保持体能时,更能体会劳动的崇高)进行文字论证(《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
八、实证锚点:当先验判断遇上脑电波与大数据
(一)康德命题的实验室检验
“无目的合目的性” 的神经机制:相关实验研究发现,当人们观赏那些被认为具有 “无目的合目的性” 的抽象艺术作品时,大脑中的默认模式网络会被激活,且激活强度与人们对作品 “合目的性” 的评分呈正相关。这表明,康德所描述的这种审美体验在神经层面有其对应的活动模式。
“共通感” 的进化基础:跨文化的审美研究显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对某些基本的审美形式(如对称的图案、和谐的色彩)的偏好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康德提出的 “共通感” 提供了进化层面的证据,说明人类可能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审美倾向。
(二)华远模型的算法实现
时空定位的量化工具:通过文本分析技术可以挖掘出艺术作品所蕴含的历史语境信息;利用环境监测设备可以获取审美对象所处空间的物理特征;借助眼动仪等设备可以记录观赏者在审美过程中的注意力分布,这些量化工具为华远模型中的时空定位提供了可操作的测量手段。
良性循环的数学模型:华远模型中的良性循环可以通过构建相关的数学公式来进行描述和计算,将审美对象的简洁性、矛盾统一度、信息冗余度等因素纳入其中,从而对审美价值进行评估。这种数学模型在景观设计、产品设计等领域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能够帮助设计者优化作品的审美效果。
九、范式之争的当代镜像:从古典美学到 AIGC 艺术
(一)康德的现代困境
算法艺术的挑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艺术逐渐兴起。DALL-E 等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图像是否符合康德所说的 “无目的合目的性”,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些图像是算法根据大量数据生成的,缺乏人类创作者的主观意图,这对康德强调的主体心灵的自由游戏构成了挑战。
审美主体性争议:当 ChatGPT 创作的诗歌获得文学奖时,人们对审美主体性产生了争议。康德认为审美是主体的自由判断,而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是否具有审美价值,以及其审美价值的来源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难以用康德的理论来解释。
(二)华远框架的适应性验证
AIGC 作品的 “信息中介” 分析:在 AIGC 作品中,输入的提示词代表了主体意图,模型参数构成了信息中介,输出的图像则是客体显现。通过对华远 “三定六位” 模型的应用,可以对 AI 绘画的价值进行评估,考虑其生成的图像在时空定位、良性循环、矛盾统一等方面的表现。
良性循环的新内涵:在人机协作创作中,“人类意图修正 - 算法迭代优化” 形成了一种新的反馈闭环,这体现了华远框架中良性循环的新内涵。人类创作者通过对算法生成结果的修正,传递自己的审美意图;算法则根据人类的修正进行学习和优化,提高生成作品的质量,两者的互动共同推动审美创作的发展。
十、水晶球框架与光缆线模型:华远对审美范畴的系统拓展
(一)水晶球框架的四重建构:互补、膨胀、切近、缓冲
华远的 “水晶球美学框架” 以 “互补、膨胀、切近、缓冲” 四模式为核心,形成对审美关系的立体诠释。这一框架与康德 “非此即彼” 的先验范畴形成鲜明对比:
互补模式:强调 “天然形式” 与 “人为形式” 的非对称共生。例如,自然界的山脉(天然中介)与人类修建的山间栈道(人为中介),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审美景观。这突破了康德将自然美视为 “纯粹美”、艺术美视为 “依存美” 的对立划分,承认自然与人文的平等共生。
膨胀模式:以 “大真大善” 的边界探索为核心,当审美对象的 “真”(自然规律)与 “善”(人文价值)突破常规尺度时,会形成崇高体验。青藏高原的雪山,其壮丽的自然景观(真)与 “圣洁” 的象征意义(善)相互作用,给人以崇高之感。康德虽论及崇高,却将其限定为 “理念超越形式”,忽视了自然规律与人文意义的动态耦合(《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
切近模式:追求主客信息的情感频率共振。观赏日本枯山水庭院时,庭院中的沙石、苔藓(显在中介)与 “禅意” 文化(潜在中介)相契合,引发观者内心的平静与思考。这与康德将主体视为 “理念旁观者” 的观点对立,凸显了主体在审美中的能动参与。
缓冲模式:通过 “空白 — 矛盾” 机制为审美系统提供弹性调节。中国书法中的飞白(空白)和一些现代艺术中的视觉矛盾,能够激发观者的想象力,延缓审美疲劳。康德的 “静态和谐假定” 难以解释这种动态平衡,因其追求 “感性与理性的固定统一”。
膨胀模式作为崇高美的核心引擎,通过 “真善同频扩张” 实现超越性:克里斯托《包裹国会大厦》以庞大材料体量(真)解构政治符号(善),突破常规认知尺度,形成强烈的审美冲击;《静静顿河》中顿河的 “永恒流动”(真)与哥萨克 “命运无常”(善)的超尺度结合,构建文学中的崇高能量体(《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但膨胀模式并非孤立存在:互补模式(如悲剧中 “必然命运” 与 “自由选择” 的共生)为其提供情感根基;切近模式(如读者对葛利高里困境的共情)强化体验深度;缓冲模式(如 “未言说的结局”)则避免意义僵化。正如华远在《关于科学性美学的互补膨胀切近缓冲水晶球美学框架和光缆线压缩橄榄型审美模式》中所言,崇高是 “以膨胀为引擎,多机制协同的动态信息中介”。
(二)光缆线橄榄型结构:审美演化的动态模型
华远的 “光缆线橄榄型结构” 形象描述了审美领域 “创新与共识” 的演化关系,与康德对 “审美普遍性” 的静态理解形成对比:
两极创新区:对应先锋艺术的 “极值探索”,如行为艺术、数字艺术等,以突破常规的形式挑战审美惯性。康德将此类创新视为 “共通感的不完善显现”,而华远认为这是审美系统的 “试错机制”,推动审美边界拓展。
中间共识区:代表被广泛接受的大众审美,如流行音乐、通俗小说等,是审美系统的 “稳定器”。康德仅关注 “普遍可传达性”,却忽视了共识与创新的互动 —— 中间区域既沉淀有效创新,又为新探索提供基础。
波性交互机制:创新区与共识区通过 “信息能量波” 实现螺旋上升。例如,摇滚乐从最初的小众音乐(两极)逐渐被大众接受(中间),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多种风格(新先锋),印证了 “创新 — 整合 — 再创新” 的审美演化规律。这比康德的 “共通感” 更能解释审美史的动态发展。
在崇高美领域,“光缆线橄榄型结构” 同样适用。以 “奉献” 这一崇高主题为例,个体自发的奉献行为(如主动助人)处于创新极,随着社会认同度的提高,逐渐沉淀为社会伦理共识(如 “奉献光荣”),而共识又反过来影响个体行为,形成 “创新 — 共识 — 再创新” 的循环,这一过程体现了华远 “良性循环” 的核心思想,也印证了 “活着就是奉献” 作为日常崇高价值内核的演化逻辑(《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
十一、对 “自由与自律” 的理解:从 “先天自律” 到 “良性循环中的自由”
(一)康德:自由即 “先天自律” 的理想主义
康德将 “自由” 与 “自律” 等同,认为真正的自由是 “遵循自身理性立法”,而非受欲望或外在权威支配。“自由意志与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完全是同一个意志”(《实践理性批判》)。在审美领域,这意味着艺术创作需摆脱功利束缚,仅服从内心的审美法则。
例如,贝多芬在失聪后创作《第九交响曲》,不为外界的评价和利益所动,只为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和对自由的追求,这种 “自律” 即 “自由” 的体现。但康德的观点忽视了现实的复杂性:人性不仅有理性,还有欲望、自私等弱点。“在法治不健全的社会,‘自由即自律’会沦为空谈 —— 商人可能借‘艺术自由’炒作伪劣作品,官员可能以‘自律’为借口逃避监督。”
这种理想主义在解释 “恶的艺术”(如宣扬暴力的作品)时尤为无力:若创作者声称 “遵循内心法则”,康德难以区分其 “自律” 与真正的审美自由,只能陷入 “道德与审美割裂” 的困境。
(二)华远:自由是 “良性循环中的弹性空间”
华远认为,自由不是 “绝对自律”,而是 “良性循环框架下的弹性空间”,需兼顾个体创造与社会影响。
艺术创作的自由:如环保主题的电影创作,创作者可自由选择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但需传递 “生态保护” 的积极意义(良性循环),不能以 “自由” 为名宣扬破坏环境的行为。
审美欣赏的自由:观众可自由解读作品(如有人从《水浒传》中看到英雄气概,有人看到暴力倾向),但需尊重作品的历史语境(时空定位),不能将现代价值观强加于古人。
这种观点更符合现实:自由与约束是辩证的。“如同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审美自由也有边界 —— 边界内是创造的空间,边界外是混乱的深渊。” 例如,网络文学的创作自由,需以 “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 为边界,在约束中实现创新。
在崇高体验中,康德将自由等同于 “理性对感性的自律”(如道德意志超越自然本能);华远则认为,自由是 “多元模式动态平衡中的弹性空间”。《暮色》中 “风雨中牵手回家的一家子”,其崇高感源于:自然力量(风雨)与人文情感(家庭)的膨胀式共振(真善扩张);自然威慑与家庭庇护的互补共生(非对称咬合);观者对 “平安” 的集体记忆引发的情感切近;“未说出口的默契” 形成的意义留白(缓冲)(《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这种自由不再是理性对感性的压制,而是多元要素的和谐共生,呼应了 “活着就是奉献,健康就是美好” 的核心价值 —— 奉献作为信息中介的必然属性,健康作为良性循环的具身化表达,共同构成自由的伦理根基。
十二、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从 “自然为范式” 到 “分类整合”
(一)康德:自然美是 “纯粹美” 的典范
康德将美分为 “纯粹美” 与 “依存美”:纯粹美不涉及概念与目的(如雪花、贝壳),依存美则与道德、功利相关(如宫殿、肖像画)。他认为自然美是 “纯粹美的最佳体现”,艺术美应模仿自然的 “无目的性”。
“一朵花的美,是纯粹的,因为我们不会想到它的植物学功能;而一座宫殿的美,是依存的,因为我们会联想到它的奢华”(《判断力批判》)。这种划分的局限是将自然美与艺术美对立:自然美 “高于” 艺术美,艺术美若想获得纯粹性,需 “去功利化”“去概念化”,这与艺术的社会功能(如启蒙、批判)相矛盾。
“康德忽视了‘人化自然’的美 —— 如茶园既非纯粹自然,也非纯粹艺术,却兼具自然的和谐与人类的智慧,难以归入他的分类。”
(二)华远:自然美与人文美的系统整合
华远打破了自然美与艺术美的界限,将美分为 “自然美” 与 “人文美”(含广义艺术美与狭义艺术美),强调两者的互动共生:
自然美的人文转化:张家界的山峰本是自然景观(自然美),通过文人的题咏、摄影作品的传播使其成为 “旅游胜地”(人文美),自然与人文相互成就。
人文美的自然根基:城市中的公园(人文美)模仿自然山水(自然美),通过合理的植物搭配、水体设计,实现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的效果。
广义艺术美的跨界:如稻田艺术,既是农作物种植的自然系统(自然美),也是人类通过设计形成的艺术作品(人文美),体现了 “生产与审美” 的统一。
这种分类更符合当代审美实践:生态旅游、城市绿化等领域的美,都是自然与人文的融合,无法用康德的 “纯粹美 / 依存美” 划分。“华远的整合思维,回应了工业文明中‘自然与人类’和解的迫切需求。” 在崇高美领域,自然美与人文美的整合体现得尤为明显,如黄河壶口瀑布的崇高,既源于其自然景观的磅礴(自然美),也源于其承载的民族精神(人文美),两者通过膨胀模式形成共振,共同构建起崇高的审美体验,这一案例也印证了华远理论对康德自然美与艺术美对立划分的突破(《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
十三、对审美诡辩与悖论的处理:从 “逻辑困境” 到 “中介化解”
(一)康德的局限:难以应对现实矛盾
康德的理论因依赖先验概念,在面对审美诡辩与悖论时常常陷入困境:
诡辩的误导:有人用 “康德说审美无利害” 为低俗艺术辩护,声称 “只要我觉得美,就是艺术”,这种诡辩偷换了 “无利害” 的内涵 —— 康德的 “无利害” 是 “排除私人利益”,而非 “放弃审美标准”。
悖论的僵局:“悲剧的快感” 是典型的审美悖论 —— 观众明知剧情虚构,却为人物悲伤(感性),又因 “体验到崇高” 而愉悦(理性)。康德只能将其归为 “理性超越感性”,却无法解释为何 “痛苦” 能转化为 “快感”。
这些困境的根源是康德的 “静态逻辑”:他试图用 “非此即彼” 的范畴(如主观 / 客观、自由 / 必然)解释审美,却忽视了审美现象的 “亦此亦彼” 特性。
(二)华远的突破:用 “信息中介” 化解矛盾
华远通过 “空白缓冲结构” 与 “时空定位” 破解审美矛盾:
诡辩的破解:针对 “低俗即艺术” 的诡辩,华远用 “信息中介的双重性” 分析 —— 低俗作品只有感官刺激(显在中介),缺乏文化意义(潜在中介),不符合 “整体性与简洁性的统一”,因此不是美。
悖论的转化:“悲剧的快感” 源于 “显在中介(悲伤剧情)” 与 “潜在中介(对人性的领悟)” 的共振,空白缓冲结构(如剧情的留白)为 “痛苦→快感” 的转化提供了空间。观众在悲伤后思考 “如何面对命运”,实现了审美升华。
例如,余华的《活着》中,福贵的悲惨遭遇(显在中介)令人同情,但读者通过反思生命的坚韧(潜在中介),获得 “珍惜生活” 的理性快感,悖论在信息中介的互动中转化为审美张力。
在崇高审美悖论的处理上,华远的理论同样具有优势。以 “奉献的利己性与利他性” 悖论为例,康德难以解释奉献行为中 “主观为己” 与 “客观利他” 的共存,而华远通过缓冲模式的 “矛盾预留意义空间” 来化解 —— 奉献行为的 “利己” 与 “利他” 矛盾,为解读人性复杂性预留了弹性空间,而 “奉献” 的价值正在这种矛盾中显现,既非纯粹利他,也非绝对利己,而是生命本能与道德选择的动态平衡(《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在芦苇丛中躲避追捕时,听见婴儿啼哭却选择冒险留下口粮,这一行为正是 “利己(求生)与利他(救人)” 矛盾的体现,在华远理论中,这种矛盾不构成悖论,而是崇高体验丰富性的来源。
十四、人类审美与动物本能的本质差异:从 “无概念普遍性” 到 “意义赋予”
(一)康德的模糊认知:动物的 “类审美” 本能
康德观察到动物的 “类审美” 行为(如雄鸟用羽毛吸引配偶、蜜蜂筑造对称蜂巢),认为这是 “无概念的普遍性” 的体现,但未深入探讨其与人类审美的本质区别。
他在《判断力批判》中写道:“动物或许有对形式的偏好,但这只是为了生存,而非真正的审美。” 这种模糊性导致后人误解:有人将宠物的 “赏玩行为”(如狗追蝴蝶)等同于审美,忽视了人类审美的精神性。
(二)华远的清晰界定:演绎逻辑与意义建构
华远指出,人类审美与动物本能的核心差异在于 “演绎逻辑” 与 “意义赋予” 能力:
动物的归纳逻辑:蜜蜂通过 “8 字舞” 传递蜜源位置(归纳经验),但无法将 “舞蹈” 抽象为 “方向”“距离” 的概念,更不能创作 “舞蹈艺术”。
人类的演绎逻辑:人类能从 “梅花绽放”(具体)推导出 “坚韧品格”(抽象),赋予自然形式以精神意义。陆游的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正是通过演绎逻辑将梅花转化为 “高洁品格” 的象征。
意义建构的层级:
物质层:如食物的色香味(动物也能感知);
文化层:如粽子的 “纪念屈原” 意义(人类独有);
哲学层:如星空引发的 “宇宙奥秘” 思考(人类独有)。
这种差异在 “工具使用” 中尤为明显:大猩猩用树枝取食(生存本能),人类却能将树枝雕刻为 “艺术品”(艺术创作),赋予工具以象征意义。华远的界定比康德更精准:审美不是 “无概念的普遍性”,而是 “用概念建构意义的普遍性”。
在崇高审美层面,这种差异更为显著。动物可能对庞大的自然现象(如雷电)产生恐惧本能,而人类能从雷电中赋予 “力量”“神圣” 等象征意义,并在对其的超越中获得崇高感。“活着就是奉献” 的价值理念,正是人类通过演绎逻辑建构的崇高意义,动物无法理解奉献的文化内涵与哲学价值,这体现了人类崇高审美与动物本能的本质区别(《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
十五、实践应用:从 “艺术哲学” 到 “多领域适配”
(一)康德:局限于狭义艺术领域
康德的美学主要解释绘画、音乐、诗歌等 “纯艺术”,对日常生活审美、科技产品美等领域缺乏解释力:
日常生活审美:康德难以解释 “一件舒适的衣服” 的美 —— 它既实用(有目的),又美观(无目的),不符合 “纯粹美” 的标准。
科技产品美:智能手表的美,既在于外观设计(形式),也在于功能的便捷(功能),康德的 “形式与功能割裂” 难以涵盖这种 “技术美”。
他的理论更像 “艺术哲学”,关注 “什么是艺术”,而非 “生活如何变美”,这与当代 “审美泛化”(如网红景点、穿搭美学)的趋势脱节。在崇高审美实践中,康德的理论也局限于自然景观与艺术作品的崇高,难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崇高(如校园升旗、医生献血),将崇高从日常实践中抽离,体现出其应用范围的狭窄。
(二)华远:覆盖生活与科技的广泛场景
华远理论的实践应用更为多元,涵盖以下领域:
城市规划:成都的 “公园城市” 建设,通过城市公园的布局(显在中介)满足居民的休闲需求(时空定位),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良性循环),实现 “居住 + 审美 + 生态” 的统一。
AI 艺术:判断 AI 生成的音乐作品的美,需考察其是否传递人类情感(如 “喜悦”)、是否符合音乐史的发展脉络(时空定位),避免 “为技术而技术” 的空洞。
生态审美: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美,既在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自然美),也在于人类对其的保护与研究(人文美),两者的良性循环让 “生态旅游” 可持续发展。
教育领域:高校的美育课程可通过 “显在中介(书法作品、戏曲表演)” 与 “潜在中介(作者生平、文化背景)” 的结合,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欣赏《兰亭集序》时,既学习其书法技巧,也了解东晋文人的生活风尚,实现 “审美 + 历史” 的跨学科学习。
在崇高美实践中,华远理论的应用更为广泛:文学批评中,分析《平凡的世界》孙少平煤矿劳动的崇高,既关注其体力付出(真)与精神追求(善)的膨胀式共振,也考察劳动与读书的互补(物质与精神的共生)、读者对其困境的情感共鸣(切近模式),以及 “劳动价值” 的开放性解读(缓冲模式);日常审美中,校园升旗仪式的崇高,体现为国旗物理飘动(真)与爱国情感(善)的膨胀式结合,仪式流程的稳定性与创新(如校史讲述)的互补,师生集体记忆引发的情感切近,以及静默时刻的意义留白(缓冲),完整呈现多模式协同的动态系统(《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这些应用体现了科学性美学的 “实践转向”:美不仅是艺术殿堂的珍品,更是改善生活的工具。
十六、美学理论的当代价值与未来走向
(一)康德美学的历史价值与局限
康德美学的价值在于:
确立了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将美学从 “认识论”“伦理学” 中解放出来,为艺术的自主发展(如现代主义艺术)提供了理论依据;
揭示了审美体验的复杂性,强调 “感性与理性的和谐”,对美育(如 “以美育人”)有启发意义。
但其局限也很明显:
先验框架脱离现实,难以解释文化差异、科技变革带来的审美新现象(如虚拟偶像、元宇宙美学);
过度强调 “纯粹美”,忽视了美的社会功能,与当代 “艺术介入社会” 的趋势不符;
在崇高美论上,局限于 “理性超越” 的线性思维,无法容纳日常生活中崇高的多元形态与动态特征(《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
(二)华远科学性美学的创新意义
华远理论的突破在于:
方法论革新:“红绿蓝三维度” 整合了哲学、文艺学、神经科学等学科,让美学从 “玄学” 走向 “可验证的科学”;
实践导向:“三定六位一体” 为城市建设、产品设计等提供了审美标准,回应了 “美好生活需要” 的时代诉求;
包容性:既解释传统艺术(如古琴、水墨画),也涵盖新兴审美现象(如短视频、VR 艺术),具有更强的时代适应性;
在崇高美论上,以 “四维动态模式” 突破线性思维,将崇高从哲学思辨拉回日常实践,解释了奉献、健康等日常价值与崇高的内在关联,为破解当代审美异化提供了路径(《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
(三)未来走向:思辨与实证的融合
美学的未来不应是 “康德 vs 华远” 的对立,而应是 “思辨与实证” 的融合:
保留康德对 “审美自由”“精神超越” 的哲学追求,避免科学实证沦为 “技术主义”;
吸收华远的跨学科方法,用神经科学、大数据等工具验证审美规律,避免哲学思辨陷入 “空谈”。
例如,研究 “传统节日的美” 时,既需康德式的哲学思考(节日如何实现 “精神团圆”),也需华远式的实证分析(通过问卷调查、脑成像观察人们的节日体验),两者结合才能完整理解节日的审美价值。在崇高美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样是融合康德的理性超越思想与华远的动态系统理论,既关注崇高的精神超越性,又重视其在日常实践中的动态呈现,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崇高美的本质与价值。
总结
康德美学与华远科学性美学代表了美学研究的两种路径:康德以先验哲学为工具,在 “主体的心灵能力” 中寻找美的根源,构建了精密的思辨体系,为美学的独立奠定了基础;华远则以 “信息中介” 为核心,在 “主客体的互动过程” 中界定美,通过跨学科方法将美学从抽象推向具体。
两种理论的差异本质是 “静态与动态”“封闭与开放” 的对立:康德将美困于 “先验范畴” 的闭环,难以应对现实的复杂性;华远则将美视为 “信息流动” 的开放系统,能更好地解释文化变迁、科技发展带来的审美新现象。
在崇高美论方面,康德的 “单线崇高” 以理性超越构建主客对立,华远的 “四维动态崇高” 通过 “水晶球框架” 与 “橄榄型模式”,实现了从 “对立、层级” 到 “网络共生” 的范式转型,其核心是 “一个也不少” 的整合,既不忽视理性的超越性,也不否定理念的引导性,更强调主客、时空、多元要素的动态平衡(《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
对于读者而言,理解两种理论的价值在于:
学会用康德的视角感受美 —— 在艺术、自然中体会 “心灵的自由”,保持对精神世界的追求;
学会用华远的视角创造美 —— 在生活、学习中运用 “时空定位”“良性循环”,让美成为改善生活的力量,在日常实践中体会 “活着就是奉献,健康就是美好” 所蕴含的崇高价值,让崇高回归生活,在平凡中触摸美的温度。
注释
① 康德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指审美对象虽无实际用途,但其形式却符合人类的认知期待,如贝壳的对称结构。
② 信息中介:指传递美的载体,包括可感知的形式(显在)与隐性的意义(潜在),如中秋节月饼的造型(显在)与 “团圆” 寓意(潜在)。
③ 红绿蓝三维度:华远提出的跨学科方法论,红色对应哲学思辨,绿色对应文艺经验,蓝色对应科技实证。
④ 光缆线橄榄型结构:描述先锋艺术与大众审美的动态平衡,两极是创新极值区,中间是共识平衡区。
⑤ 三定六位一体:“三定” 指时空定位、良性循环、矛盾统一;“六位” 包括时空、循环、整体、简洁、信息、中介。
⑥ 华远 “膨胀模式” 的核心机制:指审美对象的 “真” 与 “善” 突破常规尺度引发能量爆发,参见《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4.1.2 节。
⑦ 康德 “数学的崇高” 与 “力学的崇高”:参见《判断力批判》“崇高的分析论”,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⑧ 《暮色》“风雨中牵手” 的多模式分析:参见《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 》6.3 节。
参考文献
[1] 康德。判断力批判 [M]. 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 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M]. 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
[4]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 [M]. 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 宗白华。美学散步 [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6] 华远。关于科学性美学的互补膨胀切近缓冲水晶球美学框架和光缆线压缩橄榄型审美模式 [J]. 搜狐新媒体,2025(1):1-38.
[7] 华远。崇高美论的范式转型:从单线单程到四维动态 —— 华远与康德、黑格尔的对话与分野 [Z].知乎新媒体 2025.
[8] 华远。暮色中的崇高 [Z].百家号新媒体 2025.
[9] 《暮色》诗原文 [Z]. 2015.
[10]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M]. 金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11] 路遥。平凡的世界 [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作者为华远
写于2005年3月,修改于2025年9月
发布于:湖南省富兴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